2025年3月24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主办的“论道讲坛”系列讲座之“亲亲世界:先于本真与非本真之别”在良乡校区研教楼121成功举行。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孙向晨老师主讲,哲学院副院长赵猛老师主持,李涛老师等参与。孙向晨老师围绕海德格尔哲学的理论困境与中国哲学视野下的“亲亲世界”概念展开了一场深入浅出的学术讲座。讲座通过对比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共在”理论与儒家传统中的“亲亲”思想,揭示了海德格尔哲学中缺失的伦理生存论基础,并提出了以家庭关系为核心的“亲亲世界”作为解决路径,为理解人类存在的温暖性与伦理性提供了全新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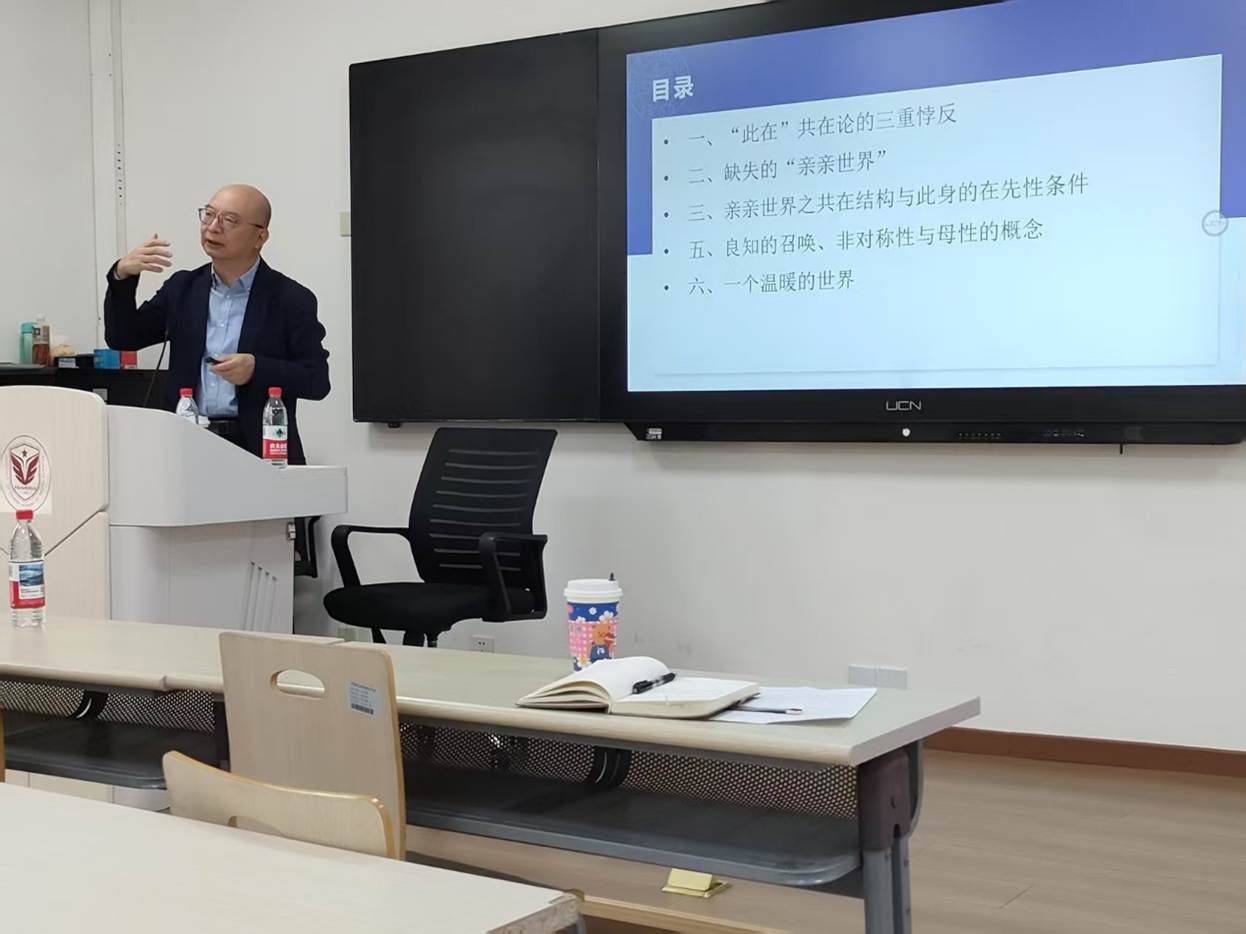
在讲座正式开始前,孙向晨老师首先指出,不同于一些西方哲学家(如列维纳斯)对于海德格尔的批评,他认为海德格尔“此在”共在论的缺失环节关键在于“亲亲世界”,这是被给予的结构,而非建构而成。孙老师也进一步指明,他将借助诸如列维纳斯“母性”等概念的援引,来阐明家庭本身包括伦理关系、世代传承等环节,这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他者。这一理解不仅包含他者的他异性,更重要的是包含他者的“亲近性”。
第一,孙老师指出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是西方哲学传统上的突破与问题。海德格尔从“我思”到“在世界之中存在”的转变打破了传统哲学主客对立的桎梏,但是其由于过度强调个体化的本真性而对于“共在”(Being with)维度阐释不足,未能揭示伦理发生的机制。这一问题根源在于缺失“亲亲世界”这一重要环节,因而导致其缺乏对于爱、信任、共情与责任等现象的生存论基础的分析,也难以为世界的温暖奠定基础。在海德格尔看来,他人是通过“工具网络”而匿名显现的,并且是以平均化的“大众”面貌呈现的。但是,海德格尔又用家(home)的修辞来表明此在建构的非个人性。所以,海德格尔的此在论陷入了一种“沉沦困境”,即一方面认为日常“共在”以“沉沦”的方式出现,但是另一方面又认为“沉沦”不是从源初状态的“沦落”。这也进而导致了一种“无家可归困境”,并导致海德格尔在一种相对矛盾的态度上使用“家”这一“隐喻”式的意象。
第二,孙老师认为,汉语世界能够为海德格尔的归家疑难提供线索,能够克服海德格尔“在家”遮蔽“家人”的盲点,通过“亲亲世界”来弥补源初共在的缺失。从中国文化传统来看,亲亲世界是生存论的出发点(“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此外,“亲亲”也是与他者关系的原型,不仅先于“用具世界”与“公众世界”,并且无可消融。所以,我们要区分家的现成性与“亲亲世界”,要悬搁“家”所属的文化与社会属性和消极性要素,进一步揭示其生存论结构。海德格尔也曾谈及“本真的结合”,但这并不是源初性结构,“亲亲世界”则提供了一种“源初的结合”。
第三,孙老师认为“此在”应该从“此身”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其可以帮助区分源初面对亲人的境况与“被抛境况”,另一方面从“身”在汉语中存在的自我具身化的指称作用、生命关联与代际来源含义(“身孕”)、牵扯父母(“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含义引出“亲亲世界”。“此”体现了空间性,既拉近了与父母的关系,也借由此关系定位自身的生存,“家人关系”让“家”作为生存论空间获得本体论地位,弥补海德格尔的缺失;“身”则显示了“世代时间”的具身化,“身体”的传承让“此身”得以“在世代之中存在”。总之,“亲亲世界”是“此身”被给予的最小共同世界,不仅让“温暖抱持”先于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畏”,并且也可以消除“被抛”的虚无主义倾向。
第四,孙老师指出,“亲亲世界”的基本共在结构是亲子(世代关系)、夫妇(性别关系)、兄弟姊妹(同胞关系),并且“爱由亲始”,是关于爱、信任、共情、责任的。亲子关系引出世代性,这不同于人的生存的“个别性”,并且以“温暖抱持”对抗“畏”;夫妇关系涉及两性协作、从情欲到伦理升华,让人们能够超越偶然性,建立持久的两性协作共在模式,超越单个性别意义上的个体主义;同胞关系体现出了一种血缘亲近,可以扩展至“拟亲”,区别出“被抛状况”与“渊源有自”。此外,“亲亲世界”也是一个在先的爱之共同体,“赤子之心”可以先于理性选择,赋予“此身”以初始信任;“亲亲世界”也可以内化“此在”的在先性条件,不仅生存的“有限性”源于依恋与脆弱,而且“此身”是从“角色-自我”开始建立关联的,而非通过“常人-自我”。
第五,孙老师认为海德格尔的伦理学的根本困境在于,海德格尔的“良知”是一种空洞的召唤,缺乏他者的维度,本真性也是缺乏伦理实践的,最终导致存在论的优先遮蔽了伦理。这一点与列维纳斯对海德格尔的批评有相似之处,即“亲亲世界”所包含的对于责任性的呼唤的前反思的给予性为伦理的发生提供了具身化的根基,列维纳斯的论述与之非常类似。但是,列维纳斯的思路是基于某种神学性思维,它是由远及近的;汉语思想传统则是奉行“道不远人”,强调由“爱亲”引发“恻隐之心”,即由近及远。此外,列维纳斯的母性概念也可以与汉语世界的“坤卦”主体传统互通,都强调出一种非生物性的具身化的伦理。但是,“身”也是“妊娠”,我与他者的关系不是面对面的相遇,而是最彻底的亲近与切近,母性也会带来无限责任(对照“赤子出胎”),是源初的伦理被给予性。

第六,不同于海德格尔的世界的“黑暗”与“在家”的“逃避”,孙老师提倡“亲亲世界”是一个温暖的世界,拥有温暖性的面向。“亲亲世界”可以以最小利益算计环境培育无条件的责任伦理,反抗诸如霍布斯基于自然状态的生存论结构。这种结构不仅为个人德性奠基,更通过“家国同构”的扩展逻辑为天下体系提供伦理范式。此外,它作为源初的伦理场域,形成不同于“自我”原则的责任逻辑,这构成了人类文明存续的隐秘根基,也解释了他者何以突破自我中心。当然,“home”不同于“family”,家不仅包括作为住所的对于“我”的保护,而是起源于“亲亲”之情的呵护与世代的传承。只有家才是世界开始的地方,才可以从“亲亲”到“亲近”,进而“家化”“内在化”世界,生发出“天下一家”的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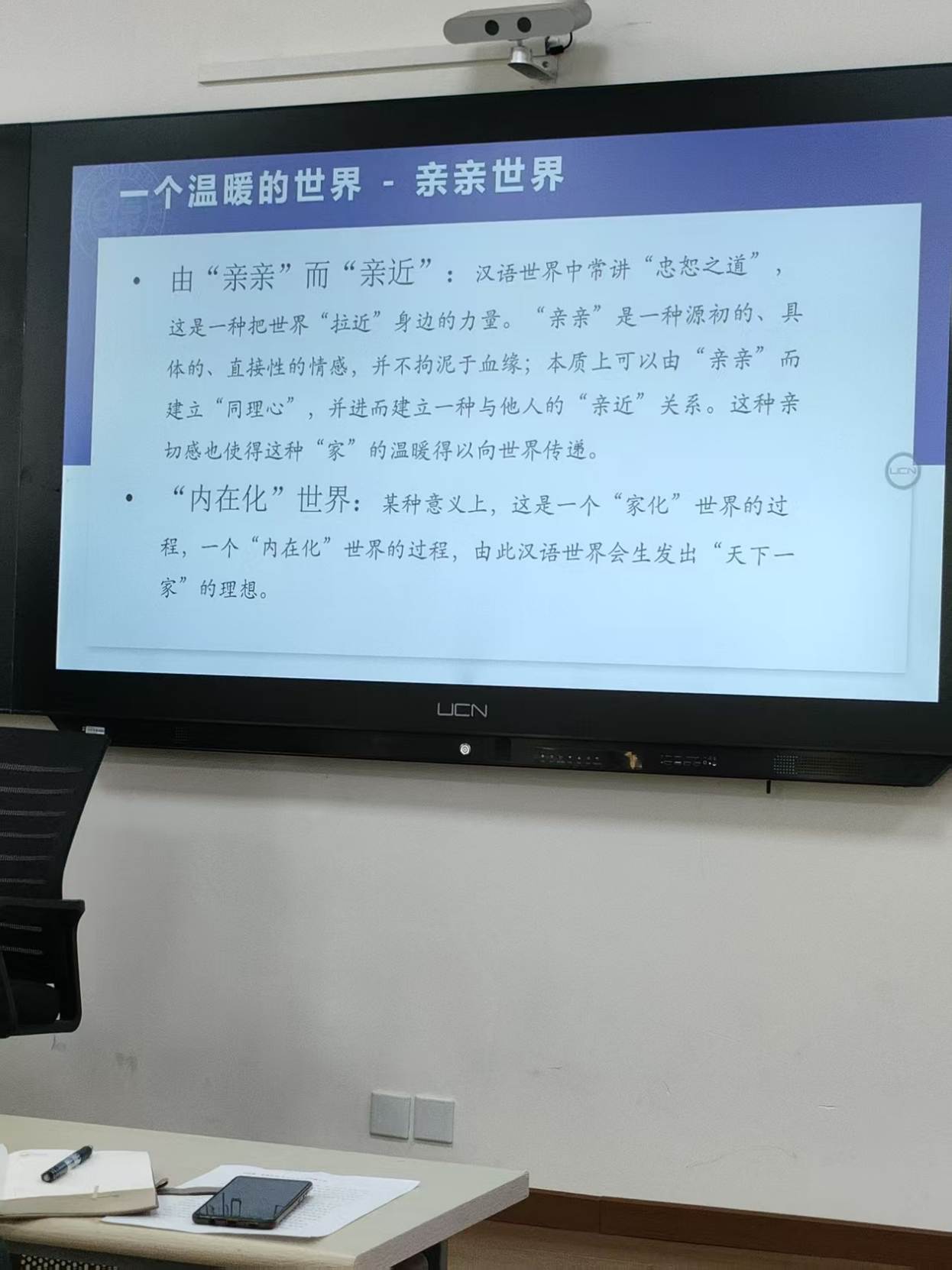
Q&A
李涛老师提问:如果以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为对照对象,是否也是兼顾爱与正义、爱与权利,且包含亲亲之爱等各种爱,如果这样对比会不会让亲亲与个体的这一对立不那么明显?
孙老师回答:选取海德格尔的原因在于他巨大的影响。当然,古代确实在这个问题上相比而言平衡很多,但也有极端情况,如柏拉图的“共产共妻”。西方思想与中国思想的重要差异在于,不是建立一个从上帝出发的秩序等级,而是世代传承。此外,哲学问题是普遍的,诸如“亲亲”等问题在西方也是存在的。
赵猛老师提问:以家建构生存论母题,其中既包含家的理想状态,与列维纳斯相联系身体性存在也必然带来一种阴暗面。在这种结合中,其何以统一?
孙老师回答:我不是在现实的意义上给出的结果,但是重点在于通过这种理想来建构一种可能性,我这里至少提供了一种在西方思想中缺失的可能性。但列维纳斯意义上的“创伤”确实表示了一种他者对我的侵害性,但重点在于这包含了回应。重点不在于痛苦,而在于对于这种痛苦的回应,这是避免不了的。
同学提问1:不同于血缘联系,该怎么理解与他国哲学家的“神交”?
孙老师回答:首先,这体现了血缘联系、身体的有限性。其次,这也体现了哲学家与大众的区分在启蒙以来的不明晰性。
同学提问2:现象学方法在您的论述中如何运用?其又有何问题(如主体性倾向)?
孙老师回答:现象学的关键在于意向对象总是超出意向行为本身,总是有东西在涌现。这个实际上中国人是可以理解的,所谓“形神”。对我而言,关键在于我们能够搁置“家”的社会性要素,回溯到生存论分析。当然,海德格尔的目的在于回到对于存在论的追问,这在中国传统中确实不明显,所以张祥龙老师曾经用“生生”来论述这一问题。列维纳斯的论述也与中国传统有差异,我在这里恰恰要强调这种“世代性”上中西文明的差异,如“发扬光大”“愚公移山”背后的世代性。
同学提问3:这里的“亲亲世界”是否可以构成一种“界”,其推扩何以可能?
孙老师回答:可以参考孟子、张载的论述,没有一种绝对的冲突存在,如“天下”论述。
整场讲座在热烈而激扬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文案:龙彦、陈永帅